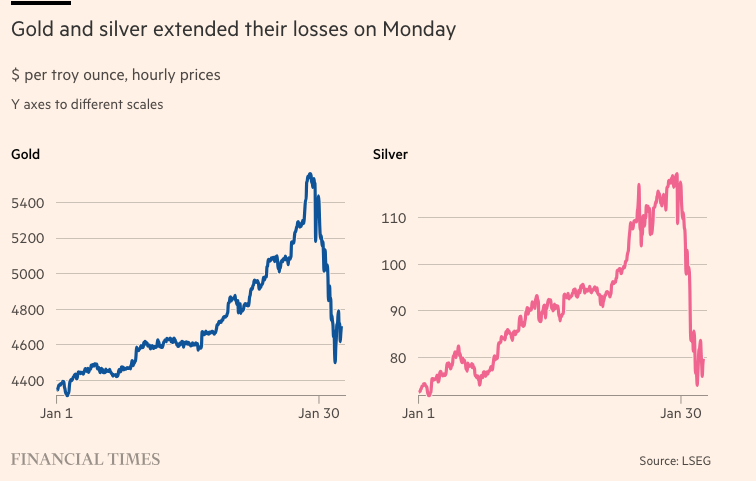研究美中合作的资深学者解释了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如何继续定义双边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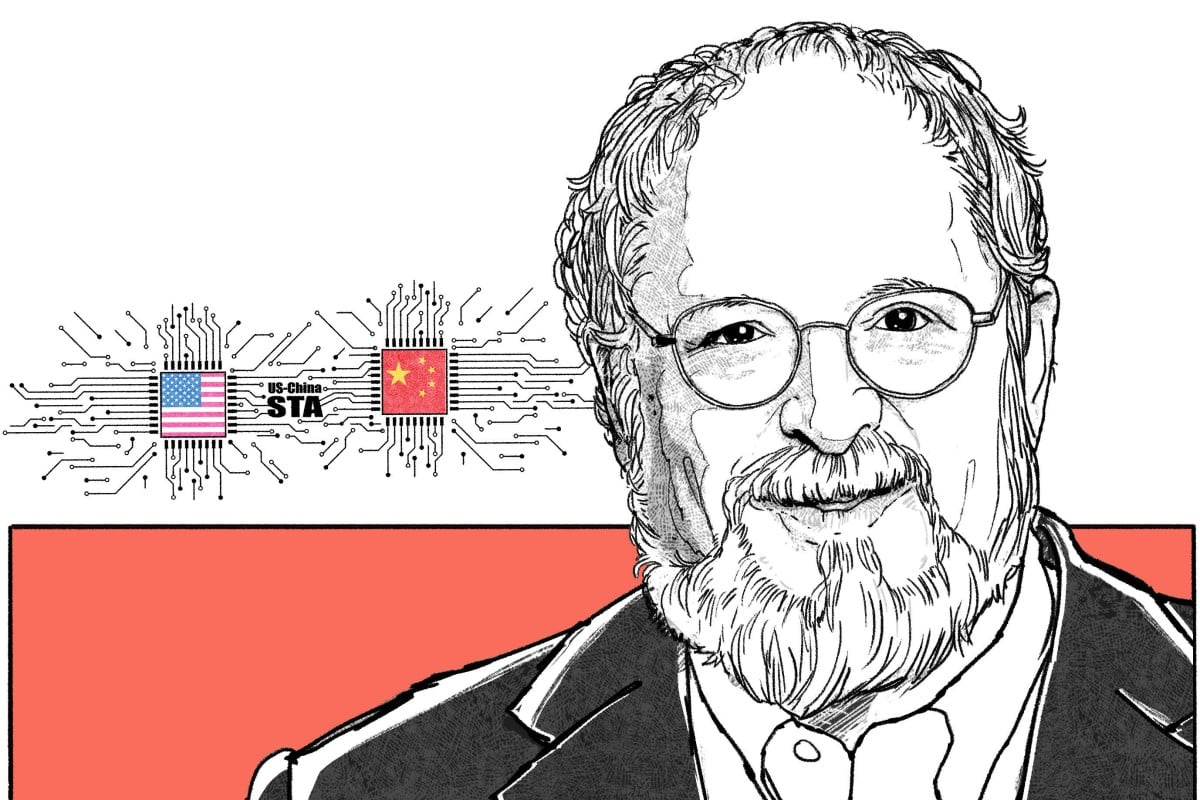
丹尼斯·西蒙是美国与中国在科技合作以及中国创新体系方面的顶尖专家之一。他曾担任过多个高级职位,包括昆山杜克大学的常务副校长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美中项目的主任。
他目前在北京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教授一门关于中国科技政策的研究生课程。这次采访首次出现在《南华早报》Plus版。
您能解释一下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核心要素,以及它在促进美中科学合作方面所起的作用吗?为什么它被认为是双边关系的基石?尤其是在当今地缘政治环境下,是什么让它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如此敏感?
《美中科技合作协定》(STA)于1979年由[吉米]·卡特政府首次签署,是管理两国官方科技合作的基础性法律和外交框架。其核心要素包括:通过部委、机构和实验室进行政府间合作;机构和学术交流,支持研究人员流动和联合项目;针对健康、农业、能源和环境科学等特定领域的联合工作组;以及共享数据、协调资金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机制。
它被认为是双边关系的基石,因为它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是美中关系正常化后的首次正式和和平的接触。在外交关系仍然脆弱的时期,科学合作提供了一个政治上“安全”的平台来建立信任。它的总体影响是巨大的——它使科学外交成为现实。
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下,STA正处于国家安全担忧(例如,间谍活动、知识产权盗窃、网络安全)、经济竞争力(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半导体领域)和技术民族主义(在双方都在增长)的交汇点。曾经使STA成功的开放性现在被一些人视为一种脆弱性。目前关于STA的讨论不仅引发了关于科学的辩论,也引发了关于美国应该与所谓的战略竞争对手进行多少接触的辩论。
在2000年代中期访问北京的代表团期间,我参加了一个圆桌会议,一位美国科学家在会上分享了清洁煤技术的突破性研究。中方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提议开展一个联合试点项目。然而,美国代表团犹豫了——担心该技术可能会被商业化,而没有得到对等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刻突显了STA促成的开放性的希望和风险。幸运的是,一项名为CERC(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的协议被签署,其中包含一份关于该项目下开发的任何新知识产权的处置的详细附录。
回顾您与中国数十年的交往,STA促成的最重大的成果——科学、文化或外交——有哪些?您能否举出您自己的互动或合作中的具体例子,来说明该协议如何塑造了美中科学交流或使全球科学受益?
STA在多个领域催化了变革性的影响。科学产出显著增加,美国和中国研究人员合著的论文数量从1980年代的涓涓细流增长到2010年代的每年超过20,000篇。在全球健康方面,在SARS爆发和Covid-19的早期阶段,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和研究机构之间先前通过STA建立的联系对于数据共享至关重要。在气候建模和排放数据方面的联合工作为两国参与《巴黎协定》奠定了基础。另一个重要的成果是为准妈妈建立叶酸协议,这显著有助于减少出生缺陷。
就个人而言,我曾经协调过一个关于纳米技术的双边论坛。中国研究人员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数据集;美国同行提供了高精度建模。这种协同效应是真实存在的——一些由此产生的专利是联合申请的。如果没有STA渠道确保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官僚和外交支持,这种合作就不会发生。

1979年1月3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华盛顿签署《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后合影。图片来源:VCG/Getty Images
基于您对中美关系的观察,自1979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STA)成立以来,它是如何适应全球科学格局和双边关系变化的?为什么近几个月来关于STA的讨论似乎沉寂下来?这是一种战略暂停、政治疏忽还是其他原因?
STA大约每五年续签一次,反映了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重点是农业、水文和能源。在21世纪的头十年,生物医学和环境合作有所增长,到2010年代,重点转向了太空、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大型科学领域。然而,最近的两次续签,分别在2018年和2023年,变得越来越困难。
从2023年末到2024年,续签讨论明显变得低调。这种沉默似乎源于战略模糊性、国内政治限制和低调外交的结合。双方都不想完全结束或完全续签该协议,这使得STA得以保持低调。华盛顿和北京都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技术民族主义压力,官员们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在幕后进行非正式谈判。
从我2024年在北京与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的谈话中,我明显感到他们对美国的沉默感到沮丧,但也理解(乔·)拜登政府正在应对充满挑战的国内环境。一位官员告诉我,“他们想保持后门打开,但又不想引起国会太多的抨击。”值得注意的是,由(约翰·)穆莱纳众议员领导的国会新特别委员会已成为对STA的最大和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这进一步使续签过程复杂化。
上个月,我们看到双方在伦敦恢复了会谈,此前唐纳德·特朗普和习近平自特朗普就职以来首次通了电话。白宫也在考虑取消一些出口管制,以换取稀土。您如何评估这些贸易摩擦与修订STA的潜力之间的相互作用?
两国高级官员在特朗普-习近平自1月份以来的首次通话后在伦敦会面,寻求建立在所谓的“日内瓦休战”的基础上。讨论的重点是稀土出口流量和放松一些美国出口管制作为交换。令美国非常懊恼的是,中国此前已停止所有稀土矿物出口,以此明确表明它也拥有真正的杠杆领域。
美国官员表示愿意放松半导体出口限制,前提是中国恢复稀土出口。稀土(用于电动汽车电机、国防系统)已成为中国战略谈判工具箱中的有力工具。
然而,更广泛的美国政策举措,例如进一步限制高科技出口和限制学生签证,表明了一种令人担忧的战略脱钩心态。尽管如此,鉴于特朗普目前显然在美方掌握大权,伦敦会谈至少表明了一种务实的重新接触,认识到相互经济依赖和风险。例如,特朗普似乎已从积极撤销中国学生签证的想法中退缩。
双边STA通常涵盖五年;虽然修订后的协议于2024年12月续签,但它仍然处于休眠和萎靡状态。然而,或许幸运的是,当前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的时机可能有助于重振STA。
积极的激励措施(放宽出口管制、稳定的研究签证)可以为重振科学技术合作协定(STA)铺平道路,该协定应强调医药健康和农业合作。鉴于特朗普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问题上的立场(“钻,宝贝,钻”),这两个曾经的优先领域不太可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重振STA势头的最大障碍仍然是挥之不去的政治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在多个领域仍然很高。 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观察家认为深度建设性解决问题的机会渺茫,特别是考虑到特朗普周围仍然有很多对华鹰派。 即使华盛顿和北京做出让步,这些让步也可能是针对特定领域的、持续时间有限的,并且更倾向于减少而不是消除主要的战略障碍。
总而言之,在现实中,中国学生和学者正在经历真正的压力——他们正面临潜在的学业和职业中断,这可能导致他们不再选择美国的项目。 这将威胁到不仅支撑着有意义的STA合作的人才流动,而且很可能威胁到美国国内的科学技术进步。
在政治上,贸易领域的有限调整(例如,稀土与芯片出口管制)为逐步恢复与STA相关的合作提供了一条狭窄的途径。 最终,深化合作的真正潜力取决于解决潜在的信任和安全问题。 修订后的STA中包含的新防撞措施确实提供了一定程度的风险缓解,但它们是否足以满足反华反对者的需求还有待观察。
鉴于特朗普政府最近采取的限制美国技术获取和吊销中国学生签证(特别是 STEM 领域学生签证)的举措,您是否在您的人脉网络中遇到过中国研究人员或学生反映这些政策对个人或职业造成损害的情绪? 这将如何影响STA的长期可行性?
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报告了震惊和被排斥的感觉。 这一举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更不用说那些已经在美学习并可能被终止学业的中国学生付出的个人代价了。 此外,目前正在申请 2025 年秋季入学签证的学生正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因为签证预约已被大量取消。 目前,中国学生占美国 100 多万国际学生的 24.6%。 他们的学术和商业贡献是巨大的:国际学生每年创造超过 500 亿美元的收入; 仅中国学生就贡献了约 150 亿美元以上。
在学术界,已有数百名中国科学家和博士后离开了美国,以回应最初的“中国倡议”下的执法行动,该倡议导致 250-300 多名中国或华裔学者失业。 初步估计,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 1400 多人。 最近一项针对华裔美国教授的调查发现,61% 的人因担心受到监视和骚扰而考虑离开美国。 仅仅是被指控犯有工业间谍等罪名,即使被判无罪也可能毁掉一个人的职业生涯。
研究跟踪发现,早在 2021 年,与中国有关联的科学家将其隶属关系从美国机构转移的比例增加了 22%。
个人和机构的动荡已经削弱了合作势头。 我们已经目睹了人才管道的稳步下降。 中国和美国学者可能仍然对合作感兴趣,但他们参与联合研究计划的意愿已稳步下降。
STA的反对者常常忽视的一个现实是,由于中国的参与,美国在许多科技领域仍然具有竞争力。
丹尼斯·西蒙
对美国在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方面的负面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很难理解特朗普政府 2.0 行动背后的道理。
STA的反对者常常忽视的一个现实是,由于中国参与美国的研发体系,美国在许多科技领域仍然具有竞争力。 扰乱美中之间的人才流动会危及美国长期的创新表现。
如果STA在创造有吸引力的联合研究机会方面消失,顶尖的中国研究人员可能会离开美国,从而导致中国制定新的举措,例如“千人计划”,以将人才导向国内,从而削弱跨境STA的可能性。
从您作为与中国学术界和专业界都有着深厚联系的人的角度来看,围绕STA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更广泛的双边关系? 美国和中国能否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其他关键技术等领域展开竞争的同时,保持强劲的科学合作?
围绕STA的不确定性已经在多个层面滋生了不信任感。 学术机构不愿启动新项目,例如联合实验室,科学家担心旅行限制和监视,资金提供者越来越焦虑,导致赠款和交流的枯竭。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但科学合作仍然以非常低的水平存在,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生物多样性等领域,因为这些问题是全球性的,需要合作。 然而,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高科技领域,合作现在受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关注。
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如何启动科学技术合作的新时代。 中国有句谚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确定第一步至关重要。
任何旨在重振美中科技合作的新举措都应侧重于共同利益与全球挑战相一致的领域,优势互补的领域以及地缘政治敏感性较低的领域。 最有可能的目标是跨国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在关于数据和个人安全的新“防撞措施”范围内运作。 新的合作还必须接受合理程度的竞争。 当然,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计算等一些领域由于存在很高的壁垒,仍然难以合作。 成功的关键将是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中立平台的使用以及逐步建立信任。
我记得在 2000 年代初期遇到一位中国博士后,他现在是深圳的一位实验室负责人。 他在 2023 年告诉我,“我很乐意再次合作——但现在,如果我甚至给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发电子邮件,我都必须解释自己”。 合作中的寒意是真实的,但重新建立联系的意愿也是真实的,这种情绪存在于太平洋两岸。
鉴于您在国际学术和科学界拥有丰富的经验,美中STA与其他全球双边或多边科学协议相比如何? 从您对中国与世界科学交往的观察中可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以了解STA在全球研究的更广泛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美中STA在范围、持续时间和象征意义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与制度化程度更高但政治色彩较淡的美国-欧盟科技协定,以及强大但很少成为双边关系核心的美国-印度或美国-日本科技协定相比,STA显得与众不同。
中国更广泛的全球科技战略反映了灵活性和务实性——它通常避免全面的框架,而更喜欢谅解备忘录(MoU)、资金联盟或项目级协议。 中国还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科学项目等举措,将科学作为一种软实力,这些项目为非洲和中亚的合作伙伴提供奖学金和实验室基础设施。
这种转变标志着中国从一个单纯的技术和诀窍进口国,转变为技术供应国和购买国。我曾遇到来自中国驻世界各地大使馆的科技专员,他们几乎就像风险投资侦察员,提供资金和合作机会。相比之下,科技部(STA)则更为官僚,但拥有无与伦比的历史和深度。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认识到,随着中国科技的崛起,它希望扩大其在国际和区域科技事务治理中的整体影响力,这也解释了它积极参与国际和区域科技组织的程度不断增加。
凭借您在中国的深厚关系,您能告诉我们中国与其他国家达成的科技协议的情况吗?这些协议如何反映中国的战略重点,又与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有何不同或互补之处?您是否在中国亲身经历或参与过讨论,从而揭示中国在对待全球科学伙伴关系上的态度?
中国的协议反映了战略重点。与德国和欧盟的重点是制造业创新和绿色能源。与以色列的重点是应用技术和农业科技。与俄罗斯的重点则越来越放在太空和核技术上。与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不同,许多此类协议更具交易性,开放性较低。
在最近于上海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听到中国科学家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描述为“母协议”,而将所有其他协议描述为“子协议”。这提醒我们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仍然具有多么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尤其是在中国高级官员中。
作为一名在美国和中国的学术合作方面拥有第一手经验的人,您在您的Schwarzman课程中强调的科技合作的核心主题或教训是什么?您在中国的个人经历如何塑造了您教授这个课题的方法,您的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与中国有自己的联系——为讨论带来了哪些见解?
在Schwarzman学院,我教授了一门关于中国科技政策的研究生课程,而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是其中的一个核心重点。我强调的信息是,在当前的国际关系时代,科学既已成为桥梁,也成为战场。中国学生通常对过去的合作水平表示热情,而美国学生则更为谨慎,担心安全和互惠问题。
我们详细讨论了最近的2023-2024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谈判,以及为什么达成一项新协议需要这么长时间。一位来自中国的学生问:“如果没有信任,为什么要续签?”另一位来自美国的学生回答说:“因为信任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讨论比许多智库论坛更富有成效,尤其是因为一些Schwarzman学者拥有STEM背景和相关的研究相关工作经验。
鉴于最近中美贸易谈判的进展,例如90天的关税暂停,您是否看到贸易缓和能够促进达成一项新的或修订后的科技合作协定的途径?根据您在中国的经历以及对中国政治和经济优先事项的理解,经济谈判会如何影响科技合作?您能否分享任何关于贸易紧张局势如何影响学术或科学交流的个人观察?
贸易缓和可能为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续签创造空间——但前提是双方都看到互利。从历史上看,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引发了一波科技合作浪潮,而2018-2019年的贸易战则引发了学术访问的放缓以及对联合项目的审查。
拜登政府关于半导体的贸易制裁使与中国的科技合作成为焦虑和担心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源。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期间,似乎不太可能在2018年续签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因为它似乎卷入了贸易战,但它仍然被续签了,尽管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或评论。
在2023年拜登政府领导下的情况甚至更加令人沮丧,因为现有的协议由于各种新出现的紧迫问题(如数据安全和个人安全)未被涵盖在原始协议中而变得过时。我们两国政府高层之间的信任已经以多种方式瓦解。然而,令我非常高兴的是,经过大约18个月的持续谈判,一项新的修订协议于2024年12月签署。我在支持续签方面非常积极。
作为昆山杜克大学的前执行副校长,您如何看待最近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与中国联系的审查,特别是对昆山杜克大学提出的指控?这如何融入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中美学术合作的更广泛背景中?您能否分享您在任职期间应对这些紧张局势的个人反思,以及它们与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挑战有何关系?
对昆山杜克大学的审查反映了对中美教育合作项目的更广泛怀疑。批评人士指责在学术自由、影响力运作、不对称的学生流动、未经批准的知识转移以及用美国价值观换取所谓的巨额回报方面做出了妥协。在我担任执行副校长的五年任期内,我看到了学生们积极的参与、严谨的课程和机构的诚信。
中国昆山杜克大学(简称DKU)成立于2013年,是由杜克大学和武汉大学合作创办的一所侧重于博雅教育的合资大学。图片来源:DKU
昆山杜克大学隶属于中国教育部。杜克大学在保持对所有学术和研究活动的持续但并非严苛的监督方面非常警惕。尽管如此,如果昆山杜克大学与其中国合作方武汉大学之间存在任何有意义的研究合作,科技协定(STA)在象征意义上通过规范合作并设定政策框架来帮助保护这些项目。
我们经常需要向达勒姆和华盛顿的利益相关者保证,合作是基于共同的学术目标和价值观,而不是屈服。科技协定以及我们的合作教育协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便在合作机会出现时进行探索。请记住,昆山杜克大学主要是一所本科博雅教育机构;它不像杜克大学本身,杜克大学是一所R1综合研究型大学。
随着有报道称,由于担心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策限制,科学家们正在返回中国,这种人才流失将如何影响科技协定和美中科学合作? 凭借您与中国研究人员和机构的联系,这对全球科学意味着什么?您认为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会改变科技协定的轨迹吗?如果会,又将如何改变?
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执政期间,诸如“中国行动计划”之类的政策导致许多中国科学家回国——不仅是担心受到监视或职业生涯受损,而且实际上已经遇到了这些问题。这种人才流动或再循环削弱了美国的科研产出,加速了中国的自力更生,并破坏了建立了几十年的合作网络。特朗普第二届政府进一步限制了签证和资金,拒绝资助与科技协定相关的项目,并使正式续签在政治上变得不可行。
最后要说的是,科技协定是美中两国如何在双边关系中看待科学外交的风向标。如果它处于休眠状态甚至崩溃,则表明从接触转向脱钩和遏制——不仅在贸易或军事事务上,而且在构建全球知识的结构中也是如此。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全球流行病和健康等全球挑战问题中,没有哪一个问题的有效解决不依赖于美中两国持续的合作。
原文链接: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316280/history-tells-us-us-china-ties-will-survive-current-rupture-neysun-mahboubi?module=perpetual_scroll_1_RM&pgtype=article